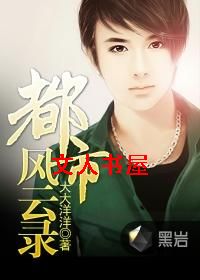艺妓回忆录-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从来没有拉过她的手——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同父母团聚了。然而,在那些幻想中,我从未真的回到家里;也许我是太害怕看到家里的真实情况了。无论如何,想想自己走在家乡的小路上似乎已经可以给我慰藉了。某些时候,我会听见睡在我附近的女仆咳嗽,或是奶奶令人尴尬的放屁声,想像中大海的气味就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脚下粗糙的泥土路也会变回我蒲团上的床单,我还是跟开始幻想前一样,除了孤独,什么都没有。
当春天来临时,丸山公园里的樱桃树都开花了,为了应付所有的樱花观赏会,初桃白天比往常更忙碌了。每天下午我都看着她为出门而梳妆打扮,我真羡慕她充实的生活。我已经开始放弃希望了,不再幻想的时候,一天早上,我下楼发现前厅的地板上有一个包裹,我就走上前看了一下写在盒子上的名字和地址:
京都府京都市
富永町祇园
新田加代子转
坂本千代收
我太吃惊了,用手捂着嘴巴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因为邮票下面写的回复地址显示包裹是田中先生寄来的。
我还没想出下一步该做什么,阿姨就从楼上下来了,她叫人拿来一把刀,割断绳子,拆开粗糙的包装纸。在层层叠叠的亚麻布中间躺着几块小小的灵牌,它们本来都竖立在我们醉屋的供坛前面。其中两块成色较新的灵牌我之前从未见过,它们上面写着陌生的法号,我不认识那些字。我害怕得甚至不敢去想田中先生为何要把灵牌寄给我。
这时,阿姨把装着灵牌的木盒子放在地板上,又从信封里拿出信来读。最后,阿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我带进了会客室。“千代,我要你读一读一个名叫田中一郎的男人写给你的信。”她的语气异常沉重缓慢。她在桌上摊开信纸时,我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呼吸。
亲爱的千代:
你离开养老町已经半年了,很快树上新一季的花就要盛开了。花开花谢的过程提醒我们,总有一天死亡会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孤儿,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你一定要承受住。你离开家乡远赴京都开始新生活的第六个星期,你尊敬的母亲就病故了,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你尊敬的父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对你痛失双亲深表遗憾,希望你能节哀顺便,请放心,你父母的遗体已经被安葬在村里的公墓中。葬礼是在千鹤镇的子角寺举行的,养老町的妇女还吟诵了佛经。我相信你尊敬的双亲已经在极乐世界里安息了。
艺伎学徒的培训过程充满了艰辛。然而,我非常钦佩那些历经磨练后脱胎换骨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人。数年前我造访祇园时曾有幸观赏了春季舞蹈,之后还参加了一个茶屋宴会,那次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很满足,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千代,艺馆可以让你免受漂泊不定的痛苦。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目睹了两代孩子长大成人,我深知普通的鸟儿极少能生出天鹅来。天鹅如果一直生活在它父母的树上就会死掉;所以那些天生丽质且天资聪颖的人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开辟一条路。
你的姐姐佐津在去年深秋来过养老町,不过她很快又跟杉井家的男孩子跑了。杉井先生急切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他的爱子,因此他请求你一有你姐姐的消息就立刻通知他。
你最诚挚的朋友
田中一郎
早在阿姨把信读完之前,我的眼泪就不断地往外涌,就像水冒出烧开的水壶一样。
当我终于可以说出话时,我问阿姨她是否能把灵牌竖在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并代我拜拜它们——因为我承受不了自己去拜的痛苦。可她拒绝了,她说我应该为自己的想法觉得羞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不管我自己的祖先。她帮我把灵牌立在楼梯口附近的一个架子上,这样我每天早晨就可以拜一拜它们了。“千万不能忘记他们,小千代。”她说,“他们是你童年所有的记忆。”
第九章
收到家人噩耗整整一年之后,早春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在四月份,又逢樱桃树开花的季节。当时我快满十二岁了,开始看起来有了一点女人味。我的身高几乎已经长足了。我的身体还是很瘦,摸上去有很多骨头,就像一根只有一两年树龄的嫩枝,但是我的面孔已经褪去了孩子气的柔和,现在我的下巴变尖了,颧骨的线条也分明起来,脸长开后眼睛呈现
出杏仁的形状。过去,街上的男人很少注意我,仿佛我不过是一只鸽子;现在当我经过时,他们开始看我了。
那天上午,阿姨在楼上叫我,要我把初桃昨晚拿错的头饰带去给她。
于是我在校舍外面等着,等着初桃出来。她却在我认出她前就发现了我,她和另一名艺伎一起朝我走来。你也许会纳闷她为什么也在学校里,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舞者了,而且她无疑通晓作为一名艺伎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事情。但事实上,即使是最著名的艺伎,也必须在她们的职业生涯里不断进修更高级的舞蹈课程,有些艺伎五六十岁了还去学校上课。我把头饰交给她,转身要走。
“噢,不要走,小千代。”初桃对我说,“我想让你看一个人,就是那边那个正穿过大门的年轻姑娘。她名叫一木美惠。”
我望望一木美惠,初桃似乎不打算再多介绍她的情况。“我不认识她。”我说。
“是的,你当然不认识她。她没什么特别的。有一点笨,和跛子一样笨拙。不过我想你会觉得有意思的,她快要成为一名艺伎了,而你却永远当不成。”
我认为这是初桃所能对我说的最残酷的话。一年半以来,我一直被迫从事女仆的苦役。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条漫无尽头的长路,走在上面看不到一丝希望。我倒不是说我想成为一名艺伎,但我肯定不愿意一辈子做女仆。我在学校的花园里站了很长时间,看着与我同龄的年轻女孩互相聊着天鱼贯而过。她们可能只是回去吃午饭,可在我看来,她们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而我却只能回去擦院子里的踏脚石。
我走到四条街并转向加茂河。南伊豆剧院门口挂着巨大的横幅,宣告当天下午将上演一场名为《且慢》的歌舞伎表演,那是我们最著名的一出戏。观众如潮水一般涌入剧院。男人们都穿着黑西服或和服,几个服饰艳丽的艺伎被衬得分外显眼,就像是浑浊的河水上漂着的秋叶。在这里,我又一次目睹热热闹闹的生活从我的身边走过。我赶紧离开大街,走上一条白川溪边的小路,可即使在那里,仍有一些男人和艺伎目标明确地在赶路。为了彻底摆脱这种想法带给我的痛苦,我朝白川溪走去,但残忍的是,连河水也在它的目标——先流到加茂河,再流到大坂湾,最后流进内海。似乎所有的地方都在给我同样的暗示。我靠在河边的一堵小石墙上哭泣。我是被遗弃在汪洋中的一座孤岛,非但没有过去,也不会有将来。不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然而,我却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怎么了,这么好的天气实在不该如此悲伤。”
一般来说,祇园大街上的男人是不会注意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女孩的,尤其是在我哭得像个傻瓜的时候。假如有个男人确实注意到了我,他肯定也不会和我说话,除非是叫我别挡着他的路,或诸如此类的事。然而,这个男人不仅耐心地同我讲话,而且态度非常友善。他对我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我是一个大家闺秀——或许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像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公平、甚至友善地对待我——在那个世界里,父亲不会出卖他们的女儿。我周围喧嚣嘈杂的人声似乎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我感觉不到了。当我抬起头看着这个跟我讲话的男人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把痛苦都留在身后的石墙上了。
这个在街上和我说话的男人有一张宽宽的平静脸庞,他的容貌非常光洁详和,让我感觉他会一直平静地站在那里直到我不再悲伤。他大概四十五岁左右,灰色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梳直。但是我无法长时间地注视他。他看上去实在是太优雅了,我只得面红耳赤地移开目光。
他的一边站着两个比他年轻的男人;另一边站着一名艺伎。我听见艺伎轻轻地对他说:
“唷,她不过是一个女仆!大概她跑腿时绊到了脚趾。我肯定很快就会有人来帮她的。”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么对别人有信心,严子小姐。”这个男人说。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真的,会长,我认为您不该再浪费时间了。”
在祇园跑腿时,我经常听见有人被称呼为“部长”,偶尔也听到过“副社长”。但是我很少听见“会长”这个头衔。
“你是想跟我说呆在这里帮助她是浪费时间吗?”会长说。
“噢,不。”艺伎说,“只是没有时间可耽搁了。我们可能已经赶不上演出的第一幕了。”
这时,会长转身吩咐那两个年轻的男人带严子前往剧院。会长留下没有走。他看了我很长时间,我却不敢回看他。最后,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她说的没错。我只是一个傻姑娘……请您不要因为我误了看戏。”
“起来站一会儿。”他对我说。
我不敢违抗他,尽管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不过我显然是多虑了,因为他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替我擦去脸上的砂砾,那是我刚才从石墙上沾下来的。站得离他这么近,我都可以闻到他光洁的皮肤上的爽身粉味。当他拭去我脸上的砂砾和眼泪后,他用手指托起了我的下巴。
“没事了……一个漂亮的姑娘,没什么好难为情的。”他说,“可你却害怕看我。有人对你不好……或者就是你的生活不如意。”
“我不知道,先生。”我说,当然我的心里其实很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得到我们理应享的福。”他告诉我说,接着他眯起眼睛,仿佛在说我应该认真琢磨一下他所说的话。
我巴不得想再看看他脸上光洁的皮肤,宽宽的眉毛,温柔的眼睛及上面大理石般的眼睑;但是我们的社会地位相差太悬殊了。最终,我还是抬起眼睛扫了他一眼,但我立刻就红着脸移开了目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不过,让我怎么描述那一瞬间见到的景象呢?当时他正看着我,就像一个音乐家在演奏前看着他的乐器,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的一部分,他能看透我的内心。我真想成为他演奏的乐器啊!
过了一会儿,他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
“你喜欢甜李子还是樱桃?”他问。
“先生,您是说……吃东西?”
“我刚才路过一个小贩,他在卖淋着糖浆的刨冰。我成年后才第一次尝到刨冰,可我像小孩子一样喜欢它的滋味。拿着这个硬币去买一份吃吧。把我的手帕也拿着,这样你吃完后就可以擦擦脸。”他说着,把硬币放在手帕正中,包成一卷,然后伸出手来让我拿。
我接过手帕卷,朝他深鞠一躬表示感谢。我感谢他不是因为那个硬币,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不怕麻烦停下来帮助我。我感谢他,是因为……嗯,是因为某些我至今都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残酷无情,我们还能找到别的东西。
当会长的身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后,我立即冲到街上去寻找那个卖刨冰的小贩。那天并不是特别热,我也不怎么想吃刨冰,可吃刨冰能延长我邂逅会长的感觉。所以我买了一纸杯淋着樱桃糖浆的刨冰,又走回去坐在石墙上吃。糖浆的滋味似乎很刺激,也很复杂,我猜这只是因为我的情绪太激动了。假如我是一名像严子那样的艺伎,我想一个像会长那样的男人可能会花时间跟我在一起。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羡慕一名艺伎。当然,我原本就是被带到京都来做艺伎的;可是在此之前,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立刻逃跑。现在,我领悟到一件被自己忽视的事情: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艺伎,而是做一名艺伎。如何成为一名艺伎……这个,不能算是生活的目标。但是,做一名艺伎……如今我意识到这是一块通往别处的踏脚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会长的年纪大概不超过四十五岁。许多艺伎在二十岁时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叫严子的艺伎大概不会超过二十五岁。我还是一个孩子,将近十二岁……可是再过十二年,我就二十多岁了。那么会长呢?那个时候他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