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望书-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荒原上走过,前往新疆,开始了他的长达八年的亚洲腹地探险。
斯文·赫定在《越过阿拉善荒原》中写道:原野总在变化着,忽而,我们又置身在长满茂密的、深绿色的梭梭树丛的丘顶上。蒙古人管这类时常长得像橡树一样的高大的灌木叫甲格或扎格,它还被赋予了另一个高贵的名字,莫多涅昆,即树王。与其他树木不一样,由于梭梭生长在干旱荒漠地区,生长期长,树的枝干在火的燃烧时不会出爆裂声;称其为“树王”的另一条原因,是它在燃烧时几乎不冒烟。
梭梭被称为最能抗干旱的树木之一。从地中海、撒哈拉沙漠,到波斯湾和中亚腹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都可见到成片的梭梭林。梭梭可长到四米多高,根深可达九米。阿拉善高原上广布梭梭林,从黄河边开始,延绵七八百公里。四十年前这里的梭梭林还有二十多万亩。斯文·赫定一行在进入阿拉善高原后第一个休息的地方叫“梭梭井”。井是在沙土地上掘出来的,水清凉甘甜。他们的驼队还在丛生的高大的梭梭林中迷了路。
令人震惊的是,现在成片的梭梭林竟荡然无存。
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株梭梭!
探险家笔下高贵“树王”哪里去了,是谁毁灭了梭梭林?
路上不断的追问,了解到,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搞工业化,大规模开发资源,修通往吉兰泰盐池的公路铁路,梭梭林被大面积的砍伐,施工队伍用作燃料——这是梭梭林在阿拉善消失的主要原因,≮我们备用网址:。。≯
我想象着荒原上的一堆堆煹火。火焰在噼噼啪啪的声音中蹿动着。烤火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筑路工人。对他们来说,夜晚的煹火是绝对需要的。可以吃一口热饭,喝一杯热水。
工业化、发展与生存总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论及荒原上的梭梭林被砍伐的时候,可能会误入一些人设置的“伏击圈”:“如果只有一杯水,是人喝还是用来浇花?”——这是“某专家”在阐述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合理时用的“惊人之语”——国家要盐,国家要修公路铁路,你总不能让筑路工人不吃饭吧?
不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吗?令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某些人,包括学者专家,都要把这些问题尖锐地对立起来,弄到有你无我的地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似乎这样才算本事。
沙漠的植被,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梭梭林更是如此。途中,听说有些地方还有小片残林,我提出看看梭梭林,结果谁没有找到一株。大片梭梭林被毁,无疑加剧了荒漠化的发展。好了,没有了梭梭林,没有了植被,草、水,你还在哪里立足?
五、月球般荒凉冷寂,养不起马的牧人才骑摩托车放牧
原先预计的一天行程,走了足足两天。
夜晚,四周荒凉冷寂,如同月球一般。
在地学上,人们将没有植被覆盖的裸地,称作荒漠,即人们常说的不毛之地。这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深入不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森林广布,只是人烟稀少、没有开发或开化罢了。戈壁为蒙古语,意为草木难生的土地,主要是沙质荒漠的砾质荒漠。去居延海途中,满目皆是的沙漠和砾石滩。
斯文·赫定比较关注自然环境的考察,而与他同行的中国考古字家和地史学家黄文弼似乎更注意西北的历史变迁。差不多在同一地点,黄文弼在阿拉善高原上的乌托海发现了石斧、石刀、鱼叉、石锥等大量旧石器。黄文弼为这一发现兴奋异常,他认为,四五千年以前,这儿有大片的湖面——原始居民很会选择地方,往往生活在水草丰美的水边,远比现在都市里的家园“亲水”。
阿拉善高原在几万年前存在过大湖,而且还是大淡水湖。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水面逐渐缩小。吉兰泰盐湖古代也是个大湖,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有记载。汉代,湖面还很宽广。现在吉兰泰等几个盐池,就是湖泊最后的浓缩。在腾格里、乌兰布和与巴丹吉林大沙漠中,近年发现了丰富的地下水,一些人又兴奋异常,认为可以大大开发,比如用来垦荒,发展种养殖业。要知道,这些深层地下水,是地质年代湖泊渗漏形成的,用一点就少一点,不可能得到补充。
现在人们说得最多的发展。发展其实是进步的另一种表述。
但一些人始终没有弄懂过发展的本质。在自然界也是如此,进步的近义词是进化,退步的近义词是退化。沙漠化本质上是一种退化。如果沙漠化扩大,还有发展吗?
首先提出“沙漠化”一词的,是法国生态学家阿·奥波利维尔。奥氏在法国政府中,任殖民部水利森林局局长,此人经常到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考察。他发现年降雨量700~1500毫米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由于不加节制的砍伐、焚烧和耕垦,使森林退化为疏林草原,疏林草原进一步退化,就会出现土壤侵蚀、旱生植物侵入等一系列现象,然后出现类似沙漠的景观。奥氏将森林不断退化的过程和结果,称之为沙漠化,或作荒漠化。
阿拉善高原的年降雨量要少得多。
我到过科尔沁、乌兰布的草原与沙地,也到过阴山下,考察过毛乌素沙漠,与这些地方比,阿拉善高原稀疏的灰绿色,简直就没有可称得上草场的地方。几十年间,荒漠化的扩展,速度实在惊人。
对于那位法国生态学家你不能不怀敬意,他提出这一论点是在19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年。
在去居延绿洲途中,我们看了几个牧点。
只有一户牧民,在公路边,离巴彦浩特也不足百里,草场的条件在阿盟算是好的。有顶帐房,也有间房子,一眼深井,但井水不能喝。主人说,这里草场退化严重,20多亩草场才养一只羊子。地上看去还稀稀拉拉地长了些草,很多草牲畜不吃,是毒草。
这家牧人也没有马,帐房外停着辆红色摩托车,非常扎眼。
和主人交谈后,我想起了过去宣传上的偏颇可笑——牧人骑着摩托放牧,好像现代生活进入牧区,是幸福的象征,那篇骑摩托车放牧的消息,还被评为好新闻。在草原上纵马驰骋,要比骑摩托方便和潇洒。至少在西套蒙古,因为草场的退化,牧人养不起马,而改骑摩托车。
中午12点多钟,我们到了苏海图村。
在中国地图上都赫然标有地名的村子,只有几间土坯房散落在公路边。据说,村子和附近的牧点,加起来有300来人,这就是一个苏木(乡)。但常年在苏海图居住的,只有二三十人。有时,村里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
公路边有一家“迎宾旅店”,三间矮矮的房子,两间可以住宿,一间是吃饭的地方,只有一张破旧的方桌和几张条凳。一条黄狗围着转来转去,主人把它轰了出去。同行的盟领导说,能吃饭的也就这个地方了,大家只好凑合着点儿。
“迎宾旅店”的老板姓甘,老家在甘肃民勤。他到阿拉善已30年了。在这里开店也有10来年了。我们十几个人一来,可把他们忙坏了。有时一天小店也没那么多客人。尽管出发前,盟里的有关部门已给苏海图村通了电话,小店里作了准备,有羊肉汤,几个西红柿和茄子。沙漠里,当然不好有过分的要求,一人可以吃上一碗面条。
端着海碗和老板娘聊天。老板娘姓魏,她引以自豪的是她的3个女儿,大女儿20岁了,在店里帮忙。二女儿18岁了,在离这里几百里的吉兰泰盐场技校。三女儿在巴彦浩特的左旗中学上初二。她说,我们都是不识字的人,到苏海图后,生活也不容易。但孩子再也不能耽误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了。
我问,这面条多少钱一碗。她说,八角钱一碗,去年,一碗六角。西红柿、笳子、葱,都是托人从左旗捎来的。这地方啥都不长。
六、一排枯树从关了门的乡邮政所院子里伸出来
不知是因为路况恶劣,还是天气炎热,离开苏海图没多远,汽车一歪,轮胎就爆了。车胎爆了的还不至一辆。其中一辆是被铁钉扎的。这沙石路上哪来铁钉?有人说,是不是修车补胎的使的坏。这路上一天没见几辆车,修车的生意很清谈。不使点小名堂,混不了吃的。后来,又有辆越野车的轮子被弯曲的铁钉扎了,对这种猜测也更坚信了。但我始终将信将疑。路况不好是事实。在这地方生活不易。挪一个地方,也比这里日子要活络得多,用不着使这么坏的主意。真的车抛在路上,几天几夜,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也很危险。
在烈日的爆晒下,换胎十分辛苦。如果路上再坏一只胎,就跑不到额济纳旗了。
从缓坡下冒出几间土房子,乌力吉到了。乌力吉也叫巴音毛道,这里有另一条路,向东通向杭锦后旗和五原。这里是老归绥——新疆公路上的一个“大站”。镇上也是一片残破,是乡政府的所在地。现在这条公路只通到额济纳旗,原先延往新疆境内的巴里坤——即历史上有名的蒲类海,现在巴里坤湖消失了,公路已经废弃。
到处是断墙败屋。零零落落的十几间房子。有补胎的。司机忙乎开了。我就进了小旅店,跟主人聊天。女老板姓陈,不到30岁,长得很水灵。她就是在这里长大的。3间客房,每间房子里都有三四张木板床,放着被褥,挺洁净的,只是被褥上落了层薄薄的土。这房屋的结构也挺特别,还有内走廊,也许是风沙大,冬天冷之故。她问我们去哪。我说去额旗。她说去额旗晚上赶不到了,住不住店?我说不住吧,有州上的领导安排。她叹了口气。她问我们从哪搭来,我说从北京。女子的眼睛放出光来:“北京,我小时就想去北京,看天安门。可一直没去过。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银川。”我说,这旅店是你家的吧,开个旅馆也不错啊,当老板,有了钱,哪儿不能去?她说,再过几年,是得要走了。我是生在这里的,过去这里的草好得很。骆驼进去,看不见身子,只听到沙沙吃草的声音。你说那草有多高?我问,你见过那么好的草?她说,我小时候,草还是挺好的。比我人高。现在,哪有什么草啊,树都死了。旱死的。镇上的人一批批的往外地走。我小学的同学,差不多全走了。原先镇上还有个邮局,现在邮局也关门了,这你一出门往南边走就看到了。镇上长住也只有一二十户。
话题太沉重。我想换一个轻松点的,便说,这么长的路上,没个歇脚的,人少,没竞争的,生意好做啊。她说,这里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没有,越来越没法活人,一路上,你看到点绿色吗?全是光秃秃的,地上连草都不长,还能长庄稼吗。要钱有什么用。一到夜里,没电灯,也没电视。还有,喝不上水。没有比喝不上水更要命的。一口井,水质也不好。到冬天,你再想想这里是什么光景。我想走。你们明年再来,我可能就关门了。
女老板给我们沏了杯水。她说,有人说,这里气候二三十年来的变化,与西边的卫星基地有关,与罗布泊的核试验有关。我说,不会吧。罗布泊的核试验早停了。她说,酒泉的基地还在发射呀。前些年有人在戈壁上捡到过金属的东西,说是火箭的残片。他们说,一发射火箭,高空大气的流向就改变了,还有不干旱的?近几年来,旱得特别厉害。
这里人来人往的,小旅店也可算是个消息总汇。这个问题太“科学”。我回答不上。
我走出小旅店,在几十米长的土路上漫无目的地走走。一眼望去,到处是断墙残壁的现代废墟,这是拖家带口远遁异乡之后,人去屋空,到处是无可奈何的没落与颓败。有几间房屋残破得厉害,只留下了几根剌向青天的砖柱。
走不多远,果然看到了关了门的邮政所,熟悉的墨绿色已开始剥落。一截土墙,墙头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杨树,全是枯死了的干枝,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剌目。杨树大约是过去邮电所职工栽的罢。这里种树也靠浇水,没人呵护,人走树死。在修车小铺子的门口,有个光屁股的孩子在土堆上爬。夕阳把孩子的胴体照得明晃晃的,像个金属做的娃娃。我心里涌上异样的凄惶。
接着的路途更加荒凉。几十里、上百里,全是黑戈壁、红戈壁,毫无生气。我到过很多地方,从青藏高原到地球的最南端——南极大陆。我要说,2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高原的大片寸草不长的土地,与它们相比,绝对不会更有生机。沙漠、砾石滩、无水的古河床、风化严重的山脊……
边界那边是外蒙古的戈壁省,渺无人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就足以让偷渡者却步。阿拉善人自豪地说,边境口岸开放后,外蒙古常有人过来,他们省长坐的车都没我们旗长、局长坐的车好,我们差的也有北京吉普,好一点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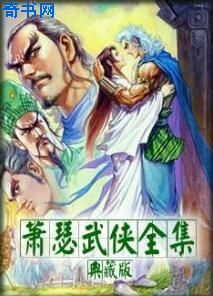

![[网王]书呆子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2/298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