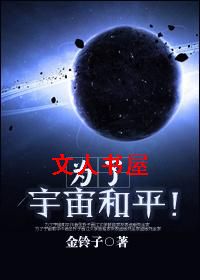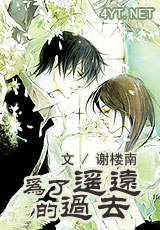为了报仇看电影-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戴着“翅膀”漫步在葡萄园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意乱神迷,根本无暇去追究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可能性。侯麦的《秋天的故事》发生在葡萄园里,几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议论着男人、爱情、生活,好像人生再无其他烦忧。《杯酒人生》的故事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产地,七天,犹如一个创世纪,七天,完成了酒喻人生的过程:友谊,爱情,温情,希望,要有什么,就有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当自小在葡萄园中长大的我,在暌隔多年后,再次看到葡萄园时,那样惊奇和欣喜的原因。葡萄园对我,曾经是触手可及的伊甸园,一旦远离,而且多年不曾接近,就渐渐成为一段连自己也都有点怀疑的过往。一个经过无数次修饰和润色的梦。当它再次出现,终于证明我所梦所想不虚。想念到此为止。
我们都知道,去往葡萄园之路,非常非常远,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找一张葡萄园的图片来,充当桌面。
《原野》一九八八年
我十三岁的第二十天
《原野》开禁的那一年,是1988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我十三岁,我回到以前住过的小镇子上,去看我的同学。在那里,那个极其破败的电影院,就要放映《原野》。那是我十三岁的第二十天,1988年8月25号。我找到了我的同学。一个是憨厚莽撞的老兄形象的那种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我称呼他为W。另一个,和我一样,高,有着少年的瘦硬的、棕色的身体,他的名字我始终记得,我叫他L。他们曾经是我的保护人,每一个中学新生,都要找到这样的保护人,组成一些秘密的、心照不宣的小小社团,以便在危机四伏、弱肉强食的中学里生存下来。现在,也还是一样。在哪里,都是一样。
他们不是我唯一的朋友,我还有别的朋友,一些更强硬、更成熟的高年级男生。我是他们的人,他们扬言,如果谁招惹了我,就有他的好看。其中一个,我至今也记得,他家距离我家不远,两家的大人在一起工作。他极其英俊,有着明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非常健壮,酷似后来日本卡通里的那些人物。他是大家的领袖,所有人都对他言听计从。他死在二十三岁,在一次并不危险的爬山过程中,他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他们用了好几天才把他的身体找全。过早死掉的,也许还有别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
我们三个,在L家外的野地里会合。那个时候是秋天,旷野上的玉米、高粱都已经成熟,还没有被收割,白杨树林子也变得金黄。我们就站在一个小小的树林子里说话,风吹树叶子的声音的确让人愉悦。我们都已很久没见,眼睛热切地盯着对方,似乎要把对方的灵魂攫取到自己的灵魂中来,囚禁,豢养。那个时候就有这种热情,没有理性的热情,初生的欲望,刚萌芽的海。根本拒绝选择,也不加以辨别。
我们去看《原野》,这个闻听已久的禁片。到小镇子上唯一一家电影院去看。那个电影院,还是三十年前的式样,《站台》里的电影院,就是那个样子。一共只有九个人,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六个附近军营里的军人。一共九个人买票看电影,所以,电影院决定停止放映。那些军人派出代表去交涉,我们等候在大厅里,这个时候,外面开始下雨。
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我,从一开始就盯着我看。那是个来自南方的、英俊的空军军官。他穿着浅色的制服衬衣,衬衣上面也许还有肩章,那时候的空军的裤子,也许是蓝色的,也许不是,我已经忘记了。总之,他穿着军人的衣服。周围的环境、气味到现在还在记忆里,而且有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唯独他是模糊的。他开始站着,后来坐下,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扳着,但是他始终在看我。那个时候我十三岁,我已经说过了,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暴饮暴食而时胖时瘦,也没有因为在酒吧和电脑前流连过久而有了一副有着色情意味的黑眼圈。那时我没有皱纹,没有疤痕留下的阴影,那个时候,我是个美丽少年,有一张洁净的脸。我很知道,从很小的时候,从他第一眼开始看我,我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为是否应该提及当时自己这种与年龄不符的早慧,这种过早的觉醒而有点犹疑,我没有别的顾虑,只是担心别人以为这是出自我的捏造。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洛丽塔》。我不再有这种担心了。
他始终看着我,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一直看着他,被一个比自己成熟的人关注,是大多数孩子的成就和荣耀。而我显然已经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理智的、庸常的关注,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足以赢得这样的关注。于是我沉浸在这种被加倍的荣耀里,犹如锦衣夜行,秘密的喜悦却一点点湮开。“下雨”造成了一个临时性封闭的、隔绝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偶然路过的人之中,因为没有后果和责任,因而暂时有了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淫逸气氛,这气氛因为双方的陌生程度而加了倍。这是一场没有丝毫危险的、发生和抑止在想象阶段的高空走钢丝、木桶飞车,没有声音的角力,是毒辣辣的阳光照在黑绿色的蜡质叶片上,塔希堤岛上的一个中午,荫凉藏在深绿里,果实上的红紫似乎可以染在手上,有人在溪流里喊叫。似乎所有的刺激都发生在想象里,而快乐并没有丝毫减少。
以下段落摘自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
从坡上下来的是个年轻人。前后挑着粪桶,一条脏毛巾缠在头上,有一张气色很好的面颊和一双有神的眼睛,双腿分担着重量从坡上走了下来。那是一个清厕夫——掏粪尿的人。他脚蹬胶皮底布鞋,穿着藏青色裤衩,五岁的我,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这种样子。那意思尚未确定,不过是一种力量的最初启示,一种昏暗的难以想象的呼唤声向我呼唤。那清厕夫的样子最初所显现出的是带有寓喻性的。因为粪尿是大地的象征。因为向我呼唤的东西与作为根的母亲的恶意的爱,别无两样。
我预感到这个尘世上有某种火辣辣的欲望。我仰望着肮脏的年轻人的身姿,那“我想成为他”的欲望,“我想是他”的欲望紧紧地将我束缚。我清楚地想到这欲望之中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他的藏青色裤衩,一个重点是他的职业。藏青色裤衩清晰地勾勒出他下半身的轮廓。它软软地颤动着,我不由地感到是在向我走来。我对那裤衩产生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倾慕。
因为,对于他的职业,我感受到某种极端的悲哀和对这烈焰焚身般悲哀的憧憬。我从他的职业中感受到极端感官意义上的“悲剧性的东西”。从他的职业,溢发出一种所谓“挺身而出”感、一种自暴自弃感,一种对危险的亲近感、虚无与活力的惊人混合感。它们逼近五岁的我、俘虏了我。也许我误解了清厕夫这一职业,也许是从人们那里听到某种其他的职业,因他的服装而错认,牵强地套在了他的职业上,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了。
一阵嘈杂从楼上传来,交涉的人获得了胜利,正在抱怨着走下楼梯,电影终于要开始了。我和朋友走进漆黑的电影院里,而他坐在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当银幕上的光足够亮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他眼睛里的光,他还在看着我们,看着我和我朋友亲昵的样子。
南海影业公司。《原野》。
他,那个彪悍的男人,仇虎,也许是做土匪发了点财,逃出监牢,带着仇恨,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像希斯克利夫一样,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仇恨从何而来,由谁而生,他只要完成自己的复仇,给自己多少年的流离、冒险、痛苦,夜里的辗转一个交代。他需要报复,只要报复就足够了。这愿望纯粹而又刚烈,根本没有一点杂质。他所要报复的人已经不在也不要紧,这愿望早就上了膛,把枪管都打磨得火红滚烫,不发都不行。
他的家乡正是秋天,原野上金红璀璨,就连他仇人的宅院,都清寂寥廓,他站在那里,似乎稍微有点犹疑。他的女人早都被迫嫁给了他仇人的后代,爱不到自己要爱的人,又长年累月地被自己不爱的人宠着,她渐渐地失了本心,向着坏女人的方向走。而这坏又没有实质内容,她担着这个名,抬着一张红扑扑的脸,在北方的原野上,摘一朵小野菊花别在头上,或者把一片木叶噙在嘴里,或者一片鲜红欲滴的浆果,都让她惊喜不已。就这么过一生吗?她没有想过,在白桦树间闪烁着她的脸。至今她也活在人群中,不难被发现。
然后爱和恨都要爆发,把秋天打破,雷雨也来了。兔起鹘落间逃亡的步子,粗重的呼吸,雨水把衣服和头发沾在额头上的那种不快,都一起来了。最后,他们看到了丛林间窄窄的铁道和他们以为再也不会看到的家乡美景,就在那里,我们感到镜头似乎倾斜了一下。他们的一生也在那里倾斜一下,这个星球甚至不会感觉到失去了一点灰尘的重量。
那电影里,有一段非常美的音乐,听过一次,就再也不能忘记。
北方原野那种让人身心舒畅的美景也是不能忘记的。
电影还是那个电影,停在一小时四十四分的地方,而看电影的人,却老了十四年。
我把DVD退出机器,那上面淡绿色的数字闪烁一下,慢慢消失掉。屋子里连一点光线都不要有。那些人,慢慢地在黑暗中一个个来了。
《为了报仇看电影…2》
内容简介
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坐在人力车上,望着车头的风车出了神,那一刹那,我懂了;黑色大丽花案发,中年妇女跑到警局去,热情地承认自己是凶手,那一刹那,我懂了;漆黑的电影院里,众人之间,我仿佛看到剧中人突然转向我,定定地望着我,单只为我说出那一句台词。有时候,看电影,是接受馈赠。因为懂得,所以成为一种馈赠,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隐秘的馈赠。或许它同时赠给许多人,但那一刻,那馈赠仿佛只属于我。
所谓馈赠,也不过是若干玻璃球、几对蝴蝶翅,我把它深藏在我的花园里,邀你同来翻检,共享喜悦。花园,在僻静小路尽头,钥匙,在你我汗湿的手中,走过去,打开。暮色里,雀鸟惊飞,红果坠地。电影,你我的秘密花园。
序 神并不承诺他何时出现
韩松落
在《为了报仇看电影》第一集的座谈会上,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要‘为了报仇看电影’?”其实,那本书的第一篇,貌似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看电影,为的是报仇,向庸常的生活报仇。”这句话也被印在封面上,在宣传活动中被频繁使用。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写的,而在回答问题的当时,我已经不这么想了,我已经不认为,电影之所以为我们所喜,是因为它五色斑斓、充满奇迹,可以供我们向生活的波澜不惊、灰暗无光报仇。在座谈会上,我的回答是:“因为电影替我们压缩了时间。即便是在它装作表现痛苦的时候,其实也遗漏和篡改了痛苦,因为痛苦是个时间概念。而电影压缩了时间。”
路内的小说《追随她的旅程》中,有一段话,就是关于时间:“那时候我觉得,《西游记》讲的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而不是路程。。。它用路途来迷惑读者,事实上它在谈论的是时间。神是不会仅仅用路途来考验一个人的。。你感到痛苦,感到在漫长的旅程中要和那么多无聊的妖怪打架,那是因为神在很远的地方。一直到旅程的最终,他们还是在打来打去,这种痛苦和漫长丝毫没有因为终点的接近而减轻,那是因为,神并不承诺他何时出现。即使你能计算出自己与神之间的距离,你仍然无法计算那个到达的时间,也许你和神只有毫厘之距,但这毫厘之间却要花掉一生的时间。”
你一望即知某个人会如何行事,仍然避免不了要和他交接,明知道某件事会怎样结局,仍然避免不了将整个过程一一经历,即便其间充满各种意外,甚或惊喜,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是,从A点走到B点,需要使用的时间,一点都不能减少。属于我们的时间,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我们需要用各种东西来充填时间,劳役、游戏、爱情,无休无止,周而复始,宛如西西弗斯滚石上山。地铁或者公交令人痛苦和厌烦之处就在这里,它把这个过程提纯了,而且毫无掩饰,它的目的是如此赤裸裸:让时间过去,让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所感受到的最大的痛苦,就来自这种赤裸的、干燥的、火星表面一样静止的时间。
电影可供我们“报仇”之处,大概也就在这里,它充填了时间,让时间比较不那么赤裸,它也加速了时间的进度,以貌似公平的方式。它之所以能让我们实现“报仇”的
![[综漫]搞基是为了毁灭世界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7/711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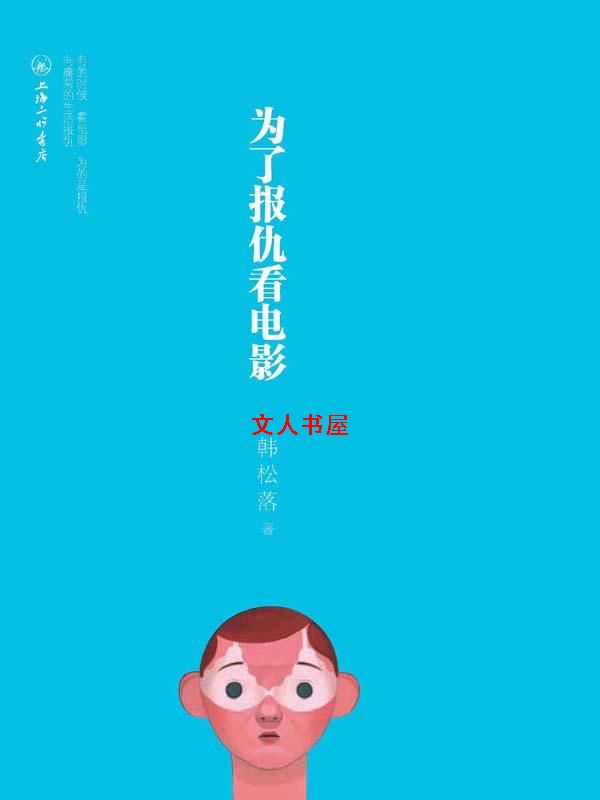
![[综漫]撒谎是为了拯救世界封面](http://www.aaatxt.com/cover/13/1384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