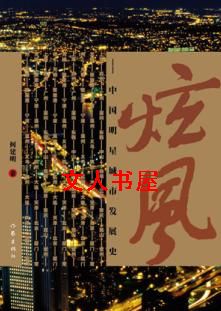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文脉-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产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云影,不知道在你的云影之外是否还有更辽阔的天宇?
——这是一种比喻。大河,比喻中国文化;云层,比喻科举制度。
自从建立科举,中国文化就与它大规模地亲密往来,后来它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没有回来;多少文人终于返回,魂魄还在考场;多少笔墨受它熏陶,变成强大遗传……
学术界在研究文化传承的时候,总是习惯于把目光集中投向学说、学派、潮流、人物。其实,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并被有效执行,那么,一个大国的行政力量就会转化成空间力量、时间力量和社会心理力量,使文化传承成为铁的事实。
中国历史上,企图成为制度的文化主张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第一项,应该是秦始皇定下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制度:“书同文。”汉武帝也想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但他毕生戎马倥偬,缺少实际执行的可能,结果只是成了一种倡导而已。真正成为一种庞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国、行之千年的,便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人类奇迹。世界上那么多伟大的古文明为什么都一一灭亡?除了历史教科书中说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原因:辽阔的领土缺少大量管理者。在一代开国雄主萎谢之后,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对此,中国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公元六世纪末开创的科举制度,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各级官吏,时间、地点、程序、内容、法禁都严格规定,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这在宏观上创造了两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国虽大,却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批官吏资源管理各方,使中华文明始终未因彻底失序而溃散;第二,普及了一种“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识,而范围又没有太多限制,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崇尚文化的气氛。
当然,负面效果也是巨大的。例如,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成了官场的附庸,两者密不可分。结果,文化的创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学能力被大幅度取消。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文人中造就了一种“科举人格”,习惯于忍耐、苦熬、投机、巴结、矫情,满口道义却远离道义,你死我活却貌似斯文,等等。
中国千余年的文风、文气、文脉,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举制度所左右。影响之深,可谓深入骨髓,于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万不可躲过科举制度。
二
让我们先回到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那几年。
在那儿,一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出于何人之口?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
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
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但是,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账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谕,废除科举。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行政管理专家。
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三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才华和学术能力的考察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多数状元诗文不佳,学问不深,这当然是真的,但做官,本来就不太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都要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那就需要为他们“创造”一种“资格”。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
做官的先天资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创造”做官的后天资格。平日见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公平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至于以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治国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这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
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有了相对统一的评判者,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开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不分贵贱的科举原则: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有人会问:难道不管道德品质?科举制度的设计者认为,道德品质要从他们做官之后的政绩上来长期审查,而不可能从科举考试中来分辨。
那么,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况且,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必须说明,科举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使得天南地北无数考生都要长久地投入这种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唐宋文学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
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有没有可能偶尔冒出两句勉强能读的诗文?依我看,千余年来堆积如山的试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但也就是这两句尚可一看,整首诗并不见佳。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科举考试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
四
伤害了文学,倒是问题不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
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
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营利性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