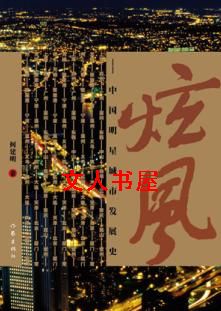中国文脉-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贵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间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唐诗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二
很多文学史说到唐诗,首先都会以诗人和诗作的数量来证明,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
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应该明白,数量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正像,现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证明这是一个“音乐的时代”。
若说数量,我们都知道的《全唐诗》收诗四万九千多首,包括作者两千八百余人。当然这不是唐代诗作的全部,而是历时一千年后直到清代还被保存着的唐诗,却仍然是蔚为大观。《全唐诗》由康熙皇帝写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写诗的数量已经与《全唐诗》差不多。因为除去他的《乐善堂全集》、《御制诗余集》、《全韵诗》、《圆明园诗》之外,在《晚晴簃诗汇》中据说还有四万一千八百首。如果加在一起,真会让一千年前的那两千八百多个作者羞愧了。只不过,如果看质量,乾隆能够拿得出哪一首来呢?
宽泛意义上的写诗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经学会造句的人只要放得开,都能随手涂出一大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当代很多繁忙的官员出版的诗文集,在字数、厚度和装帧上几乎都能超过世界名著,而且听说他们还在继续高产,劝也劝不住。这又让我想起了乾隆。他如此着魔般地写诗,满朝文武天天喝彩,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员大胆上奏,劝他不必以写诗来呈现自己的治国才能。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绝句——
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不可为。
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
对此,今人钱钟书讽刺道,李慎修本来是想拿一点什么东西去压压乾隆写诗的欲焰的,没想到不仅没有压住,连那东西也烧起来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从这蓬火,我们也能看到乾隆的诗才了。但平心而论,乾隆的诗才虽然不济,却也比现在很多官员的诗作清顺质朴一点。
说唐诗时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对应,但这不能怪我,谁叫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个人的诗作数量来与《全唐诗》较量呢!
其实,唐诗是无法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杰出诗人手中也已经不能了。
这是因为,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温热。
三
论唐诗,首先当然是李白。
李白永远让人感到惊讶。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对他的惊讶,恰恰来自于他的惊讶,因此是一种惊讶的传递。他一生都在惊讶山水、惊讶人性、惊讶自己,这使他变得非常天真。正是这种惊讶的天真,或者说天真的惊讶,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们在他的诗里读到千古蜀道、九曲黄河、瀑布飞流时,还能读到他的眼神,几分惶恐,几分惊叹,几分不解,几分发呆。首先打动读者的,是这种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后随着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发现景物果然那么奇特。
其实,这时读者的眼神也已经发生变化,李白是专门来改造人们眼神的。历来真正的大诗人都是这样,说是影响人们的心灵,其实都从改造人们的感觉系统入手。先教会人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发现、怎么联想,然后才有深层次的共鸣。当这种共鸣逝去之后,感觉系统却仍然存在。
这样一个李白,连人们的感觉系统也被他改造了,总会让大家感到亲切吧?其实却不。他拒绝人们对他的过于亲近,愿意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这也是他与一些写实主义诗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给人的陌生感是整体性的。例如,他永远说不清楚自己的来处和去处,只让人相信,他一定来自谁也不知道的远处,一定会去谁也不知道的前方,他一定会看到谁也无法想象的景物,一定会产生谁也无法想象的笔墨……
他也写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可以让任何人产生亲切感的诗句,但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既然如此思乡,为什么永远地不回家乡?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拥有足够的自由,偶尔回乡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位写下“中华第一思乡诗”的诗人执意要把自己放逐在异乡,甚至不让任何一个异乡真正亲切起来,稍有亲密就拔脚远行。原来,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属于陌生。
为此,他如不系之舟,天天在追赶陌生,并在追赶中保持惊讶。但是,诗人毕竟与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乡拥入怀抱。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一要素,是酒。“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都道出了此间玄机。帮助他完成这种精神转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诗了。
对于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为一个永远的野行者,他当然很喜欢交朋友。在马背上见到迎面而来的路人,一眼看去好像说得上话,他已经握着马鞭拱手行礼了。如果谈得知心,又谈到了诗,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他与杜甫结交后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见一斑。
然而,与杜甫相比,李白算不上一个最专情、最深挚的朋友。刚刚道别,他又要亟亟地与奇异的山水相融,并在那些山水间频频地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他老是想寻仙问道,很难把友情作为稳定的目标。他会要求新结识的朋友陪他一起去拜访一个隐居的道士。发现道士已经去世,便打听下一个值得拜访的对象,倒也并不要求朋友继续陪他。于是,又一番充满诗意的告别,云水依依,帆影渺渺。
历来总有人对李白与杜甫的友情议论纷纷,认为杜甫写过很多怀念李白的诗,而李白则写得很少。也有人为此做出解释,认为李白的诗失散太多,其中一定包括很多怀念杜甫的诗。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且也有可能确实是如此。但是,应该看到,强求他们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毕竟是相当不同的两种人。虽然不同,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友情领域的同等高贵。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地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经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四
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相差十一岁。
很多年前我曾对这个年龄产生疑惑,因为从小读唐诗时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无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则温良醇厚,恂恂然一长者也,怎么可能是颠倒的年龄?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在读者心目中对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这种年龄形象,与实际年龄常常有重大差别。
事实上,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十一岁,而且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那就是,他们将分别代表安史之乱之前和之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乱之前大多已经写出,而杜甫的佳作,则主要产生于安史之乱之后。
这种隔着明显界碑的不同时间、身份,使他们两人见面时有一种异样感。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无以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采飞扬。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时全然着迷,被李白的诗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他却很难看错。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便能立即做出判断。杜甫让他惊叹,因此两人很快成为好友。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王者之尊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就是他们的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到哪儿去打猎呢?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稀世大诗人纵马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著名诗人高适。高适比李白小三岁,属于同辈。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我不知道他当时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听到李白前来,一定兴奋万分。这是他的土地,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至,比杜甫还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六岁。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的地方当着县尉,张罗起来比较方便。为了他的这次张罗,我还特地读了他的诗集——写得还算可以,却缺少一股气,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诗人一比,就显得更平庸了。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也有几个能写写诗。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与李白并驾齐驱;贾至带来的那些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那个大泽湿地,野生动物很多。他们没走多远就挽弓抽箭,扬鞭跃马,奔驰呼啸起来。高适和贾至还带来几只猎鹰,这时也像闪电般蹿入草丛。箭声响处,猎物倒地,大家齐声叫好,所有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猎人,更像追逐嬉戏中的小孩。马队中,喊得最响的当是李白,而骑术最好的应该是高适。
猎物不少,大家觉得在野地架上火烤着吃最香最新鲜,但贾至说早已在城里备好了酒席。盛情难却,那就到城里去吧。到了酒席上,几杯酒下肚,诗就出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即席吟诗的不是别人,居然是李白和杜甫,连高适也只能躲在一边了,真是奢侈至极。
近年来我频频去陈留、商丘、单县一带,每次都会在路边长久停留,设想着那些马蹄箭鸣、那些呼啸惊叫。中国古代大文豪留下生命踪迹的地方,一般总是太深切、太怨愁、太悲壮,那样的地方我们见得太多了。而在这里,只有单纯的快乐,只有游戏的勇敢,既不是边塞,也不是沙场,好像没有千年重访的理由,但是,我怀疑我们以前搞错了。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无论是诗的个体、诗的群体、诗的时代都是这样。没有生命力的典雅,并不是我们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