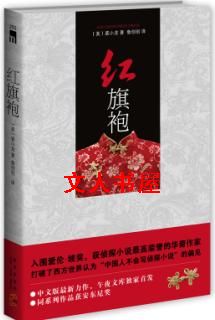蓝旗袍-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人冷不防受到惊吓,手里的碗失手落到床上,撒了一床的小米稀饭。“俺的娘唉!傻小厮你存心要吓死嫂子呀!”
小高定睛一看,那人却是玉翠,躁得满脸通红。
玉翠瞅着他的窘态嘿嘿地乐,“净想着香衣,难道就不想嫂子?”
小高被人窥见了心事无地自容,干脆闭上眼睛。
“得,不想就不想呗,嫂子有你哥稀罕着,倒是香衣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香衣本来想亲自来伺候你,可她一个新寡的女人不方便,就哭着喊着让俺来,被她缠得没办法,就只好来了,要不,俺才懒得管你的死活哩。”
第一章 宝石蓝 雪花白 麦子黄 10 洗晦
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一场连着一场。明天肯定又是一个洁净的世界,如果雪永远不化该有多好,白香衣这样想着,又想起大病初愈的高原,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对她礼敬有加,客气里带着敬而远之的冷淡。白香衣在失落之余,又很欣慰,她认可高原的这种姿态,可以避免许多闲话。她很有信心,既然障碍没有了,高原向她表白是迟早的事,她只希望那一天不要来得太急,毕竟孔宝柜刚死了没有几天。
玉翠嫂子却心急如焚,几次三番要去找高原,为他们捅开这层薄薄的窗户纸,都被白香衣拦住了,她的意思是最少也要为孔宝柜守个一百天,全一下夫妻一场的情分。
躺在被窝里,白香衣默数着这是第十七天高原没走进这间屋子了。她体谅高原的难处,没有了孔宝柜,高原没有了堂而皇之走进这间屋子的借口。
天刚麻麻亮,大街上忽然响起了一个男人大声骂街的声音,一句一个臭婊子,听得从梦中惊醒的白香衣从心底里嗖嗖地冒凉气。她又听见许多人踩在雪上的咯吱声,经过她家的屋后,渐渐地远去。白香衣忽然就心里发紧,心神不宁。
去学校的时候,白香衣迎面碰上孔树林家的。这个女人满脸的兴奋,拉着白香衣的手大惊小怪地说:“出事了,村里出大事了!孔怀才家的偷跑了,这不村里的男人们都帮着去找了。正好雪地里留下了她的脚印儿,估摸她跑不远,肯定会给逮回来,这下可够瞧了,孔怀才发下狠,非打断她的腿不可。”
“怎么会有这种事?说跑就跑了。”白香衣明知故问。
“还不是被孔怀才打跑的,说起来这娘们也够可怜的。哎,对了,听说前些天她去过你家,出来时眉开眼笑的,那天她没跟你露要跑的意思吗?”孔树林家的像发现了新大陆,兴致更加高涨起来。
“没有,别瞎说,这不是闹着玩的!”
白香衣有些慌张,急于离开,孔树林家的却死拽着她的手不放。
“就跟俺一个人说说,俺又不告诉别人。她到底露没露?”
“我都说没有了,你再问也还是没有!”白香衣气得脸色煞白,甩脱了她的手,顾自走开。
“你看你,俺又没说啥,你生哪门子气?”
白香衣听见孔树林家的在身后忿忿不平,停住脚步,回头尽量和颜悦色地说:“我不是生气,是有些着急,怕耽误了上课,婶子,别在意。”
“不在意,俺才不在意呢!”孔树林家的脸拉得差点儿跌到地上,身子一拧麻花似的,一抡风甩给白香衣一个大屁股。
一上午,白香衣替玉爱担惊受怕,满心期盼着她能跑掉。到了下午,玉翠来找白香衣,二话不说,拉着她就走。白香衣说:“嫂子,别闹,我还要上课呢。”
玉翠说:“先让小高上着,咱一块去洗澡去。”
出了学校,玉翠压低了声音对白香衣说:“孔怀才的女人跑掉了,男人们顺着脚印找到火车站,听车站的人说,她坐今天早上四点的车走的。她原是从窑子里出来的,怪不得孔怀才那样打她,该!活该!”
听说玉爱成功跑掉了,白香衣心里一宽,但玉翠咬牙切齿连声说出的几个该字,就像扯着风声的大棒槌,狠狠地敲在她的心上。
“从窑子里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有脏病,下面流脓,浑身长疮。这不,大伙商量着去镇上洗澡呢,预防传染上脏病。”玉翠继续愤慨地说:“这个挨千刀的孔怀才,脏女人不跑,他还不肯说呢,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俺记得还和那脏女人拉过手呢,一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白香衣哭笑不得,心想如果玉翠知道了此时她拉着的人也是从窑子里出来的,会不会一蹦三尺高,一蹿三里远呢?白香衣挣了一下,脱开了玉翠的手说:“我不去洗澡,要传染早传染上了,还等得到现在?”
玉翠着急了,面红耳赤:“不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是没有啥脏病,和这样的娘们住一个村里,也会粘上些晦气吧?总该洗洗吧?走走走,听嫂子的没错!”
白香衣终于拗不过玉翠的拧劲,和几个女人一起跑到王家镇,泡了一下午的澡堂子。躺在温热的水里,看着氤氲的水汽,听着女人们义愤填膺地大骂那个脏女人,白香衣恍若隔世。她不敢想,如果她的底细一旦暴露,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以前孔怀才往死里打老婆,恨得俺牙根痒痒,这才知道,那娘们该打!”玉翠死劲地搓和玉爱接触过的那条胳膊,搓得要滴出血来了,仍然不肯松劲。
“也是呢,这种娘们最靠不住,水性杨花,你看吧,说跑就跑,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孔树林家的正用指甲大小的一块香胰子在脸上小心翼翼地擦,因为说话激动,香胰子滑出了手,掉进了池子里,慌忙蹲下身子,满池子里摸胰子。
“我觉得她也是逼不得已,谁能受得了那份打?”白香衣听不过,为玉爱鸣不平。
“白老师,这就是你不对了!被男人打两下,就兴家也不要了,夫妻情份也不念了,跑出去再找野男人,这还算人吗?牲口才胡配乱配呢,人就得啥一啥终的。”玉翠抢白道,这是她第一次对白香衣严厉。
“你是说从一而终?”白香衣讪讪地说。
“嗯,嗯,就是这话,俺不会说,却知道那就是跟一个人就要一跟一辈子,一条道走到黑。”玉翠也觉得说话冲了些,便缓和说:“俺知道你是可怜她总挨打,可是这种女人就欠揍,值不得可怜。俺原来也可怜她的,这会儿只嫌孔怀才打得轻。”
白香衣点点头,不再言语。
胡桂花受用地坐在池边,闭着眼睛泡着,自鸣得意:“俺早就看出她不是好东西,躲得远远的,就是都传染上病,俺也没事。”
“瞎咧咧!那你来洗啥?老鸹嘴一张,就没好话,咋就你没事,别人有事了?”孔树林家的第一个反驳她,她没找到香胰子,惋惜得肉疼,正没好气。“还说躲得远远的,她刚来的那阵子,谁屁颠屁颠的往人家跑,上赶着认人家干姊妹的?”
“你才瞎咧咧,凭啥俺赶着认她干姊妹?俺还没贱到那份上!”胡桂花瞪开一双泡子眼,撇撇嘴说。
“你不贱,是你嘴贱!你说你拐了人家多少天津大麻花?难不成都进了狗肚子?”孔树林家的一边和胡桂花斗嘴,一边继续打捞她的香胰子。
“是进狗肚子了,你就少吃了?”胡桂花反唇相讥。
玉翠不胜其烦地说:“别唧唧歪歪,为个不要脸的娘们值得吗?要俺说,那会儿谁都没少去,后来谁想去也去不成了,人家孔怀才不稀罕你们去,见天关着个门,谁都甭想进去。哎哟哟,你摸俺脚指头干啥?”
“找俺的胰子呢。”孔树林家的扭回头,又往别的方向摸去。
“别瞎折腾了,就那么丁点儿东西,估摸早化了。”玉翠劝道。
孔树林家的充耳不闻,继续摸来摸去。到洗完澡,也没找回那块香胰子,在回去的路上别的女人兴高采烈,仿佛晦气真的一洗而光,惟有她郁郁寡欢。
女人们洗得很仔细,洗得浑身发出死鱼的白,手脚都泡皱了,才意犹未尽地爬出浴池,穿衣回家。
望着路两旁白茫茫的原野,白香衣轻轻地舒气,她想:雪是好东西,可以掩盖一切的肮脏,只可惜,不能长久,终究会化掉的。现在知道她底细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也许她能够隐瞒一辈子了。
第一章 宝石蓝 雪花白 麦子黄 11 占巢
玉翠前脚刚进家门,后脚白香衣慌里慌张地闯了进来,一张俏脸紧绷着,毫无血色。
“嫂子,我家失盗了。”不等玉翠问,白香衣就抖着嗓子说。
“丢啥东西了?”玉翠悬起了心。
“不知道呢。我自个儿不敢进去。”白香衣见了玉翠便有了主心骨,没那么慌了。
“走。”玉翠二话不说,抄起一根扁担,一阵风似的出了门。
“就咱俩人能行吗?”白香衣跟在后面,有些担心。
“甭怕。大白天的,这贼胆子也太大了,最好他没走,俺先给他吃一顿扁担。”玉翠毫不含糊地说。
“还有俺呢。”一个童稚的声音在她们身后响起,她们回头一看,却是春生紧握一根竹竿,跟在后面。
“滚你娘的蛋,你个小东西不顶用。”玉翠嘴里笑着骂,眼神里却闪着赞许的光。
到了白香衣家,玉翠放慢了脚步,嘘了一声,蹑手蹑脚地进了院子。白香衣紧紧跟在后面,心悬着,腿脚发软。
院子里没情况,屋门在黯淡的黄昏里,仿佛一张掉光了牙的老人嘴,黑洞洞地大张着。
春生初生牛犊不怕虎,首当其冲窜进了屋,玉翠随后也进了屋,四下搜了搜,没见有人,屋里的陈设也都整整齐齐,没有洗劫过的零乱。玉翠回头对白香衣说:“白老师,进来吧。不像招了贼的样,别是你出去忘了锁门,自己吓自己吧?”
“可院门上的锁明明被人砸烂了。”白香衣这才走进屋,点起洋油灯,看看箱子笼子都锁得好好的,松了一口气,诧异地说:“怪了,真的没事。”
玉翠揣摩说:“没准那贼砸了锁,还没来得及偷东西,就被人冲了。”
“嫂子说的在理,虽然没丢什么东西,可想起来怪怕的,我都不敢自个儿住这间屋子了。”白香衣说着,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瞧你那点儿出息!……”
玉翠正要借机打趣白香衣,春生忽然嚷嚷起来:“娘,白老师,你们看,炕上躺着一个老疯厮!”
玉翠和白香衣向炕上看去,目瞪口呆。可不是吗?炕上睡着一个满身泥巴的人。
白香衣毛了,下意识地往玉翠身后躲。玉翠悄声说:“别出声,看俺先给他一扁担!”
“看俺的!”不等玉翠轮扁担,春生舞着竹竿就冲上去了。
炕上的人翻身坐起来,一把抓住了竹竿,骂道:“小王八羔子,俺是你老爷爷,你也敢打?”
玉翠定睛一看,这邋里邋遢,胡子眉毛花白一片,一脸的皱纹纵横着凶相的老头不是独眼龙孔怀才是谁。白香衣也曾和他打过照面,因为玉爱的缘故上了心,也认得他。
“春生,回来。”玉翠知道孔怀才向来无赖,不讲道理,怕他伤着春生,忙叫春生。
春生却倔强地使劲攥住竹竿不松手,想从孔怀才手里把竹竿夺回来。孔怀才狡黠地嘿嘿一笑,一松手,春生后退两步,摔了个屁股墩。春生强忍不流下泪来,一骨碌爬起来,鼓着腮帮子,拖着竹竿跑了出去。
眼睁睁看着儿子吃亏,玉翠比自己挨了两个耳刮子还难受,情急之下,竟干瞪眼,张口结舌说不出话。
白香衣质问:“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和孩子较什么劲?有什么话,对大人说。”
“说得好,小骚娘们,俺来就是要和你好好说道说道。”孔怀才呲着满嘴黄牙,用那只独眼恶毒地盯住白香衣,让白香衣从骨头缝里冒凉气。
“是人你就先从炕上滚下来!”玉翠缓过劲来了,破口大骂:“那是你睡得地方吗?当爷爷的睡到孙媳妇的炕上,你是二皮脸呢,还是根本就没脸没皮?”
“啥爷爷孙子?八十杆子都打不着了,俺还忌讳这个?俺老婆跑了,她男人死了,正好凑合成一对,这热炕头俺睡定了,你气也是白搭。”孔怀才翻翻独眼的眼皮,故意伸了个懒腰。
“你老婆跑了,碍人家白老师啥事?你也不到尿罐子里照照,牲口栏里的驴粪蛋儿也比你排场。别在这里屎壳郎打喷嚏——满嘴喷粪了,哪来的滚回哪儿去!”玉翠嗤之以鼻。
“那你问问姓白的,俺老婆跑,碍不碍她的事?俺听人说了,那婊子敢跑,全是她的主意。俺不找她找谁?她让俺没了暖被窝的,就得用她自己的身子赔。”孔怀才振振有词,干脆又无赖地仰面朝天躺在炕上,唾沫蛋子满天飞。
“我没有,你老婆跑不关我的事,别血口喷人。”白香衣急忙辩解,但她心虚,说得理不直气不壮。
“谁说的?谁说的?”玉翠咄咄逼人,“你听谁说的?把他叫来,说说啥时候白老师给你老婆出的主意,他要是说不出,俺先撕了他那没有把门的嘴!”
“你甭问谁,横竖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错不了。倒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