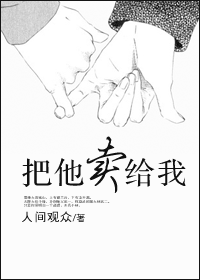给我顶住-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还能有什么事?”赵蕾笑一下,娉婷而去。
周瑾挎着小包急急走出来,关山平迎上去。
“真的不行,我得回家。”周瑾说:“我爱人在家等我呢。”
“那改天,明天怎么样?”
“明天也不行,明天我们做账,得加班。”
“你是不愿意跟我出去?”
“不是,真的是没时间。”
“那算了,不求你了。”
“真对不生,你别生气。”
“我没有气。”关山平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要不去,那张票就让它作废,别再给别人。”“不会的。”周瑾充满歉意地说。
关山平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瑾站在人群中看着窗外,手把扶杆身子随着车身的运动轻轻摇晃。窗外是一片片车流和人群。一对对情侣手拉手在便道的树荫下走,飞跑着过马路,忽然对视着笑起来……
她回到家里,各间居室内悄无人息。她脱了鞋,把包丢在沙发上,换了睡衣穿着拖鞋在屋里四处走动。
她在厨房里切肉切菜五彩绚丽地堆满一只只盘子。锅里的水开了,咕咕冒着热气掀动着锅盖。
电动排风扇飞速的旋转,嗡嗡作响。
炒勺里的油热了,冒出股股青烟,蓦得火苗窜起,油锅着了火,连忙将炒勺端下,关了炉火。
她拿着一袋挂面往滚开的锅里下,用筷子搅迅速变软变曲泛出白沫的雪白细长的面条。
那一盘盘搭配得十分悦目的肉菜原封未动,鲜灵的色泽黯淡下来。她端着一碗面条坐到电视前,边吃边看,电视机里正在播送新闻:会议、水灾和农田长势。
她吃着吃着,突然不动了,侧耳缔听,直到楼道内的脚步声过去,才继续吃。夜里,我回到家里,见电视仍开着,节目已经播完,屏幕沙沙闪着雪花,她躺在沙发上是睡着了。
我经手轻脚过去关了电视,刚要走开,她骨碌从沙发上坐起来,睡眼惺松地问:“几点了?”“第二天了。”我说。她噌地站起来,登登走进卧室,往床上一倒,拉过毛巾被盖在身上,扭身向里闭眼睡觉。
“生气了?”我讪笑着跟进卧室说。
她不吭声。我到卫生间又洗又涮,弄得浑身水琳淋的,拿了条毛巾回到卧室,浑身上下边擦着边笑说:
“不是去找‘情儿’么?怎么没去?”
“你就等着瞧吧”。她嗡声嗡气地说。
“别这样,”我上床去板她。“别不理人呀。”
“别碰我!”她使劲拧回身子。“我要睡觉了。”
我下了床,把毛巾扔到一边:“我是为了让你心理平衡才玩这么晚的。”“你少来这套!”她翻身坐起气冲冲地嚷,“我怎么啦我怎么啦?不就是晚回来了一天,用得著你这么颠过来倒过去的说?你要这样我就天天晚回来。”
“我来哪套了?我又怎么啦”我申辩,“我不也就晚回来一天。”“你是晚回地一天么?哪天你按点回来过?”
“那我也没别的呀,就是和一帮朋友打打麻将还是赢多输少。”“谁知道你天天干嘛去了。”
“你说我干嘛去了,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你干嘛去了自己知道。”
“你怎么不讲理阿?行,我不说了,你说我干嘛去了我干嘛去了。怎么着吧?”“你现在是越来越狂了。”
“什么话!我狂?我哪有你狂呵?你多狂呵,说灭我就灭我,我一个挺大男人每天还得看你脸色。”
“你要是不愿跟我过了,烦我了,你可以走。”
“就会来这套,你们女的是不是都这德性?”
“没新鲜的,图新鲜你找别人去。”
“你要老这么没完,我可真烦你了。”
“烦就烦,烦就离婚。”周瑾用被蒙头倒下。“你威胁谁呀?谁怕你呀?”“没错,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要离真离,别光说——
你要有志气,别到时哭天汕地好骂我是陈世美。”
周瑾真的哭了,蒙着毛巾被的身子一抽一抽。
我打开台灯,拿张报纸躺到床上看起来:“你哭什么呀?有本事别挺横的人?”周瑾的哭声更大了。我不理她,点上一支烟,继续看报纸:“你小点声呵,人家邻居可都睡了。”周瑾一骨碌爬起来,到卫生间又擦泪又揩鼻涕。片刻,眼睛红红的回来,照着镜子端详自己,不住的泣噎,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以为我不敢离就觉得自己怪不起了。”
“你什么不敢呀?中国人里数你有骨气了。”
我一个猛子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没抓周瑾,她冲出门,旋风般地消逝了。“你回来!”我在楼梯口大声喊,转回屋换鞋穿衣服,咬牙切齿地骂:“这个该死的,二百五、没头脑、神经病——说跑就跑。”我一溜烟下了楼,在楼区花园四处寻找,每棵树后,每辆车里都找了个遍,无人迹。夜风很凉,吹得我汗一阵阵下去又一阵阵上来。我顺着马路来到大街。街口有一个瓜摊,看瓜的老头没睡,正坐在小椅子上摇扇乘凉。我问大爷看见一个穿睡衣的女的没有,大爷说沿着大马路走了。我沿着灯光通明空无一人的大街追了一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仍没发现周瑾,便折了回来。我回到楼前,见屋里亮着灯,便飞速冲了上来,进了屋摔上门就喊:“有本事你别回来。”
屋里亮堂堂的毫无动静,我各屋看了看没有人,回到卧室躺下。我气坏了,躺半天倒也睡着了。
“周瑾!”我一声大喝。
正和赵蕾笑盈盈地从一家商店出门的周瑾吓了一跳,原地呆住。我疾步走上去,牢牢攥住她的手腕,满脸堆笑,柔声说:“跟我回家去。”“我不!”周瑾一脸凛然用手掰着我的手。“放开我,我不回家。”赵蕾在一旁微笑地看。
“有话咱们回家去说。”我死死攥住她,低声下气来说,“回家怎么说不成?”“我就不回家,不回去了,这不是正中你意么。”
我和周瑾在街上扭来扭去,引得一些行人观望。
“咱别在街上拉拉扯扯,让人笑话。”
“嗬,你还怕难看?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别给脸不要脸呵。”我手暗暗加劲儿。
“你才不要脸呢,放开我!你干嘛?”周瑾嚷。
“你干嘛?”两个联防队员过来,指着我手。“放开放开。”
我手触电般地松开,周瑾拔腿就走,我忙把她拉住。对气汹汹的联防队员们说:“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子吵架。”
“你们是两口子么?”联防队员问周瑾。
周谨不吭声。赵蕾忙说:“他们是两口子,我可以作证。”
“两口子吵架也别在街上吵呵。”
围观的群众笑,联防队员走开。
“你就跟他回去吧。”赵蕾劝周瑾,“别闹了。”
“我下午还得上班呢。”周瑾说。
“我帮你请假。”赵蕾笑着把我们俩往车站推。
我一进家门,把门一关,指着周瑾就嚷:“你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吗?差点让人把我当流氓逮了。”
周瑾不吭声,神态得意地往沙发一坐,伸手去开电视,电视刚出现一个画面,就被我啪地关上。
“你还挺得意,你占什么便宜了?我要让人当流氓逮了,你就是流氓家属。”周瑾不看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喝。
“给我倒杯水,我也渴了。”我命令道,在她身边坐下。见她没反应,就夺过她的杯子喝。
“你害怕了?”她望着我说。
我差点没让水呛着。咽下一口水说:“我害什么怕?你还以为……我是为你担心,大晚上一个人跑出去,你不知道白天街上都有坏人?”“你不就盼着我被坏人捉了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去,你好清静……再找。”
“别这样,你别这样,周瑾,我是那种人么?”
“你是什么人?”“你是真惹我生气,昨晚你气我一夜还不够?”
“你气?我还气呢。”“我气上还加着担心,心都快碎了。”
“你得了吧,气你还能睡得着觉?”
“我睡了么?那也是气着气着迷糊了,你昨晚回来了?”
周瑾抹泪:“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甭管我出什么事,你该睡照睡,亏你睡得着。”“好啦好啦。”我和解地说,“咱们别闹了,老这么闹日子就没法过了。”“你压根就不想好好过。”
“你这么说不愧么?我还怎么好好过?我都快给你当孙子了。长这么大我跟谁服过软?跟你我连自尊心都不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人总得讲理吧?昨晚我招你了么?”
“对,你没招我,你总有理,我老胡搅蛮缠。”“好好,算我无理,我不对,全是我的错。”
“什么叫算你无理?”“好好,我真无理,真混蛋,不该惹你生气。”
“你要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我一直没敢别的样儿呵。”
“你瞧你,又不认错了。”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一错到底一坏到底。”
“你现在就是坏,一点不哄我,看着我哭。其实好多时候我本来没事的,就是想闹点脾气,我不跟你闹跟谁闹?你哄哄我就好了——可你就是不哄!”
“闹吧闹吧,下回你有脾气就跟我闹,我当受气包……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我当受气包应该、光荣,别人想当还不行呢。”周瑾先是瞪眼后是破涕面笑。
“闹什么呀?”我也笑,接着语重心长地说,“你说有什么可闹的?咱们是多好的一对,郎才女貌,旗鼓相当,我种田你织布,多少人羡慕?咱们自个儿真应该珍惜。”
“一点都不好。”周瑾断言。
“怎么不好?”我忙说,“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很好了。好得不能再好了,我就是当皇上,也选你当粉头——
六宫粉黛的头。”“你少拐着弯骂人。”周瑾振振有词地说,“好什么呀?人家年轻夫妇天天去出玩,逛公园看演出下馆子。咱们呢?打结婚你就再也不带我下馆子了,一场电影也没看过。”
“我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一脑袋资产阶级思想?讲吃讲穿那是咱小市民的本色吗?”
“本来嘛,讲吃讲穿怎么啦?人家还没老呢。市民就不能享受了。”“你见哪个小市民像你说的那样?不全是吃饱了混天黑闷蜜蓄窝子炕上整点俗人乐?”
“叫你说的那么恶心,就是有人嘛。那街上一对对的都是哪儿蹦出来的?”“那不都是没结婚的?你跟他们比?”
周瑾盯着我半天没说话,脸一扭,叹气说:“结婚真没劲。”
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眼睛汪汪地解释:“我困了,昨晚没睡好。”“那你去睡好了。”周瑾冷冷地说。
“你还气么?你要气我就不睡。”
“我不气了,你去睡吧。”周瑾不耐烦地说。
我把手塔在她手上,堆着满脸笑:“咱们一起睡。”
“行了,”周瑾抽开手说,“你就敞开去睡吧,免了这套。”
我睡了整整一下午,睡得死去活来,在梦里又是打仗又是逃跑,直到黄昏,才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地起床,迷迷糊溯摇摇晃晃地出了卧室。周瑾正笑眯眯地坐在错暗的室内看电视。电视里播的是一部动画片:四只小老鼠排着队趾高气扬地从一只睡觉的小花猫身边走过,边走边齐声叫嚷:“老鼠怕猫,这是谣传。一只小猫,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它打翻。千古偏见,定要推翻。”猫和鼠都稚气十足,憨态可掬。“走吧。”我边穿衣服边对一动不动盯着电视看的周瑾说。
“去哪儿:”她回头看我一眼说。
“下馆子。”我套好汗衫说,“我也豁出去了。”
周瑾望着我,脸上露出微笑。
“乐啦?”她不好意思地笑,噌地站起奔进卧室手忙脚乱的梳妆打扮。“咱别进太贵的馆子。”
“当然,我这点理智还是有的。”
我们选了一家中档餐馆大摇大摆走进去。尽管中档,但也是冷气炊座什么的,在我看来就很好了。
“标准就是低档宴会的标准呵。”我翻看着菜单对周瑾说。
“你就点吧。”周瑾兴致勃勃。
我把服务员叫过来,点了几个猪肉做的菜。
“这几个菜够吃么?”我点完菜,服务员不走,说:“我们这儿菜的量都小。”“够吃。”我说,“我们是吃过饭来的。”
“再要个虾吧。”职务员指菜单说,“我们这儿虾不错。”
“你什么意思?”我在椅子上转过身,面对着服务员说,“嫌宰得不过瘾?”服务员拿起菜单飞快地走了。
我对周瑾说:“我就说过,落到这帮人手里,没好儿。”
周瑾干笑:“她也是好意。”
“好意?”我瞟着冷柜前抱肘叉腰站着的一排服务员。“瞧她们那架式,一个个都跟杀手似的。”
周瑾笑,低头摆弄光秃的碗筷。
我们百无聊赖地等着菜,服务员穿梭不停地往各桌上菜,就是没我们的。我几次叫住给我们开票的服务员问,她都不耐烦地回答:“正炒呢。”当她又一次如此回答时,我耐心消逝了,怒吼起来:“怎么着?瞧不起人是